枯草新芽──再見陳舜臣
(6/17路那@偵探書屋)
文學作品的影響力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我會覺得陳舜臣為什麼會轉往歷史小說?就是他的小說寫作一直以來都是以推理跟歷史這兩條線並進為主,我覺得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意識到這樣的小說在推動記憶、在讓大家瞭解歷史事件,或是採取更多不一樣觀點的方方面面上的作用。在這本《戰後文壇推理史》裡面,山村正夫是某一屆推理作家協會的會長,他本人也有寫作,他寫了一本比較接近回憶錄的東西,在這本書裡面,他提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意識。他跟陳舜臣好像還不錯,有一次陳舜臣拜託他轉交一封信給某出版社的編輯,那封信的內容就我的理解,是陳舜臣在抗議出版社的編輯沒有給他跟其他作者一樣的待遇,對他來說重點並不是待遇的多寡,而是在於這種行為背後所引申的,對於作家評價的問題,根據這一點,他想要婉謝出版社的稿件邀約。在這裡面,山村正夫寫到一段話我覺得滿有趣的,他說整封信裡面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陳舜臣寫了一句話︰「士為知己者死,作家為懂得欣賞的人寫作。」因為他本身也是個作家,所以這句話撼動他滿深的。以日文來說這是非常工整的對句,不好意思我中文翻譯比較平庸一點,但大家應該可以catch到那個意思。所以我覺得陳舜臣他其實非常非常高度意識到作者跟讀者之間的關係,還有身為一個作者,他對讀者的影響是什麼?他其實是想要透過他的文字去改變一些觀點。
陳舜臣自己有編了一本《Who is 陳舜臣?》,在這本書裡面他其實有談過他在寫作時,他是在講歷史小說,但我覺得推理小說應該也適用。他說總共有三種觀點可以去寫作,第一個當然就是敘事者,當事人本身經歷的觀點;第二個是其他人對他行為的評價;再過來是第三個觀點,就是超脫這一切之上,針對背景去做大的投影的視角。這是夫子自道,但我覺得是滿準確的說法,如果大家看過陳舜臣的書,差不多兩本以上,大概就可以理解到他這個說法基本上就是他創作的根據。他所有的小說基本上都是放置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而且他會用他的視角去解析背景,用一個比較簡單易讀的方式,可能不是一個正統史學家會同意的方式,但是是一個簡單易讀,而且對於我們這樣的凡夫俗子來說,是一個相當具有吸引力的說故事方式。我到現在都沒有辦法忘記他的《諸葛孔明》,我後來想了一想是為什麼,我想應該是因為他用了一個非常棒的商業邏輯去解釋,所以從這裡面你也可以看到一個人的背景對他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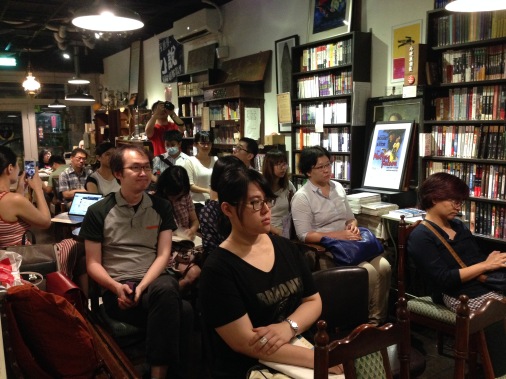
陳舜臣作品中的重要元素︰貿易、戰爭、間諜
大家都知道陳舜臣是商業世家出身,他本人也做過幾年的商人,所以貿易這件事情對他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也不太會像傳統士大夫對於錢不屑一顧,叫它「阿堵物」之類的,比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他反而會認知到貿易其實是人類非常重大的行為,推動交流很重要的力量,他是比較正向去看待它。所以他非常多的小說中,不只是歷史小說,甚至是推理小說裡面,他會直接用貿易商、貿易事件,進行跨國的事件鋪陳。比如說《埋葬南十字星》好像就是跑到南美洲去做貿易、進出口,我不太確定,但我印象中他好像把屍體放在寒天裡面,在裝滿了寒天的貨櫃裡面,突然之間有一具屍體,滿獵奇的。他的路線圖真的是非常豐富多彩,從喜瑪拉雅、新加坡到南美洲、印度,反正這個世界上只要有貿易的地方,如果給他時間的話,我覺得他多多少少都會寫得到。貿易這件事情在他的小說裡面,一直都是核心的存在,怎麼樣去解讀貿易這件事情也是。
再過來還有一點是戰爭,戰爭的陰影也是無所不在。我今天來講座之前,其實有問過一些朋友說想聽什麼,因為我覺得我想跟大家講的陳舜臣的東西都已經全部寫出來,那我到底還要講什麼?我朋友就說可以講一下他同時代的人、同時代的作家,當時是在什麼樣的氛圍裡面,陳舜臣有沒有受到這個氛圍的影響。我覺得這真是個太好的主意了,所以就開始去查。
陳舜臣是1961年出道,在那之前有一個非常鼎鼎大名的人,也是我由愛生恨的人,就是土屋隆夫。土屋隆夫跟他算是前後期的關係,甚至還有一些我們更熟知的作家,夏樹靜子在他很後面,戶川昌子差不多跟他同一個時間點。陳舜臣不是非常喜歡交際的人,但他在1962、1963年時有去參加一個會。那個會叫做「不在場證明俱樂部」,那是出版社編輯邀請當時的新銳作家入會,互相給予support的一個支持團體。他們有跟一樣是在1962、63年,由同一家出版社的編輯支持成立的女性作家為主的團體,以仁木悅子等人為核心發展出來的團體,一起活動了一段時間,每個月聚會一次,大家彼此聊聊天鼓勵創作這樣。但這個會沒有持續非常久,後來因為編輯的調動,還有裡面的作家各自生涯發展,有些人跑去寫其他東西,不寫推理小說,陳舜臣後來也跑去寫歷史小說了,所以後來這個會就有點自然而然解散掉。這個會是他目前比較可考的文學社團活動情形,當然他後來有加入一些日本比較大的團體,像是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相關的活動狀況是什麼,可能還是要再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1960年到底是什麼樣的時代?那是日本歷史上相當風起雲湧的時代,1960年代的開端是新安保法的抗議。美國在冷戰時期要防止「邪惡的蘇聯」和「邪惡的中共」破網而出,所以下定決心要補好第一島鏈,就想到了日本。那時候的日本還受限於戰後的和平憲法,沒辦法有武裝,美國就說我讓你們慢慢正常化,給你制定新安保法,你們就是和平為目的的國家,來當我的小弟吧!這件事情我不覺得日本是反對的,應該比較是他們的作法太粗糙,有點像我們的三秒過服貿,大家都火大了,上街抗議的這些人是不是全部都反服貿?不是,有一大部分人是,但有一大部分的人是覺得「這個國家可以這樣搞,這世界上還有王法嗎?」我覺得這整個新安保法的運動,基本上也是由這兩群人組成的,這對於一個時代的開端來說算是相當轟轟烈烈。畢竟大概也是戰爭結束之後二十幾年了,戰後嬰兒潮這個世代正在讀大學的時間點。在這中間,推理小說有一度迎來了它的高峰熱潮,那就是松本清張。松本清張50年帶的時候出道,開始寫一些批判日本社會現象、美國跟日本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
其實我覺得戰前出生的作家跟戰後出生的作家,對於國際關係的觀點,還是會有一點微妙的不同。像陳舜臣在小說裡頭沒有少提過戰後的經驗,但他的手法比較不是那種會讓你意識到,他常常都是靜水流深的狀態。我在寫導讀時反反覆覆看了很多次《憤怒的菩薩》,突然之間才意識到「這裡面有間諜!」我想說天啊,明擺在那個地方,第一頁他就告訴你有間諜在那個地方,我卻讀了兩、三遍之後才天眼打開,我那時候就想說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我真的有在看書嗎?為什麼會這樣?我覺得就是因為他都敘述的相當若無其事,不會讓你意識到這有什麼特別,感覺就像日常生活,間諜就在你身邊,你身邊就是有間諜。但是戰後的作家……我一時之間舉不出什麼例子,不知道逢坂剛的《卡迪斯紅星》算不算,他寫西班牙,西班牙也是有日本赤軍分子,1960年代從日本逃到歐洲大陸,自己成為一個東方恐怖分子。他們在寫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意識感的差距是存在的,想要強調它什麼樣子的程度,還是想要讓它隱沒到什麼樣的程度,這中間是有世代上面的差距。
作為世界人的陳舜臣
60年代的開頭是這樣轟轟烈烈的開頭,而60年代的結尾也是轟轟烈烈的結尾,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安保鬥爭,安田大講堂抗議事件。我一開始認識這事件是從村上春樹的小說裡面,看小說多重要!我那時候去查,就想說當時的大學生也太酷了,怎麼這麼帥氣,當然這個帥氣背後也是有很多破滅啦,他們的集體精神遭到很大的創傷。村上春樹是我高中的讀物,那時候的理解跟現在的理解有非常大的一段差距,特別是在自己去參加過一些運動之後,那個感受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會覺得有經過那樣子的一個創傷、那樣子的集體經驗,那對整個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整整一個世代。所以為什麼像是野百合,我們到現在都還會提,這一群人現在是我們社會的中堅,但是關於野百合的小說……文學小說當然一定是會有,紀錄的散文啦、詩啦,這類的創作是不少,但是大眾小說的記憶層次,我們在這個部分上某種程度會有種隔閡、斷裂的東西存在,其實滿可惜的。
所以看到這樣風起雲湧的時代,我就很好奇陳舜臣在這樣的時代中,小說創作有沒有受到什麼樣的影響,我回去看了我覺得……沒有耶!對不起這是一個非常反高潮的答案,但是我暫時只能給大家這個答案。我覺得他是非常專心致志地在寫他想要寫的東西,講述他想要講述的過程,但他是不是無視於這樣子風起雲湧的變化呢?其實我覺得他不是,他一貫的立場都是一樣的,只是外界的反應跟他一貫的立場之間怎麼對話,需要對於諸多文本的評量。
你去看陳舜臣的認同、對於國族國家之間關係的討論,其實我會覺得他從戰前到戰後,他努力試圖去效忠國家,像我們一般人一樣,你會覺得不管我們現在認同的是中華民國、中國還是台灣國,你會有一個群體的概念在那裡,疆界的概念、主權國家,我們是什麼什麼人,有這樣的東西存在。我覺得陳舜臣不是沒有努力去嘗試過,但他發現他的時代經驗、他的時代背景、他的整個人生,沒有辦法被套到那樣子的框架模子裡面去,那是做不到的。所以後來他找到了一個最適合他的框架,就是一個地方性的概念。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你要去講他到底是什麼人,這件事情是超級尷尬、超級難回答的問題,很難給他找到一個準確的定位。但我覺得他自己有幫他自己找到,就是他對於故鄉的眷戀,不管這個故鄉是統轄在誰的管轄之下,這點對他來說是沒有差的。從故鄉出發,如果去掉國界的話,這個地球會變得怎樣?這個世界會變得怎樣?我覺得到後來這反而是他關注的焦點。
陳舜臣的小說裡面到處都是所謂的邊緣人,以我們台灣為例的話,最基礎的答案可能就是1949年以前來的漢族我們會稱作台灣人,這可能是最普遍的答案,這也是構成我們社會最主要的存在。但如果陳舜臣活在現代,他如果在台灣寫作的話,我覺得他會跑去寫在中永和那個地方,有一條緬甸街,那裡有緬甸來的華裔居民,或是他可能會跑去寫泰國人。在任何國家都會存在少數族裔、少數族群,少數族群來的方式、原因、背景,還有他們為什麼在這個地方落地生根、他們跟原來母國之間的關係。這中間的多樣性,我覺得就是因為陳舜臣他本人的身分,所以他特別會關注這個部分。
你會看到在他的小說裡面,這樣子的人反而成為主角,一般會變成配角的存在,被他拉到舞台中間來,他幾乎所有的小說都是以這樣的人作為書寫的主題、書寫的焦點。他會去討論說,當一個人的生活經驗如此豐富時,這點是非常重要的,通常我們在談論多國境、跨國界的旅程時,非常習慣會用離散的概念去看他們,但是離散某種程度上是被迫的、流離的、被驅逐的,帶有悲情的創傷經驗。但我覺得在他的小說裡面,這樣的東西被壓到非常少的地步,他顯現出來的是一個更加積極向上的面向,就算他是不得不流亡到這個地方。

比如說在《黑色喜瑪拉雅山》中,有一個記者在喜瑪拉雅山採訪後來死掉了,偵探是一個被丟在那個地方的公司職員,在日本的母公司告訴他說這邊的分公司倒了,他是業務員,公司就跟他說我們沒有錢讓你回來,你就自力更生吧!在這樣的狀況下他就在那裡遊蕩,他其實是被扔在那裡的,但你在整篇小說裡面其實不會覺得他很絕望,他反而是一種「既然都這樣子了那我就在這邊玩一玩吧!」開始想盡辦法進行窮遊之旅,要去找他的朋友結果發現他朋友死掉,就開始調查,最後在尋獲真相、解謎一切之後,不只修補了他自己本身的失意頹喪,還找到繼續前進的力量。
所以我會覺得對於陳舜臣來講,離散、流離這樣的被迫狀態,並不完全是負面的經驗,他也不希望別人把它看成是只有負面的經驗。我覺得陳舜臣是有意為之要把這樣的處境,一般人會覺得你流離失所、沒有國家的保護,好像很可憐的狀態,他跟你說不是,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生存的方式,我們有我們自己生存的力量。甚至說你覺得我流離嗎?沒有啊我就是神戶人,我就是認同這個地方,我就是在這個地方土生土長,我愛這裡。他在《Who is 陳舜臣?》裡面其實有講很多,他在講耶律楚材時,以這個角色為主體去寫作時,他有談到語言問題,因為耶律楚材原本是遼人,遼被女真滅掉,然後女真再被成吉思汗滅掉。耶律楚材跟成吉思汗之間的對話還滿有意思的,那種觀點和想法某種程度上可以折射出陳舜臣這個人,在面臨比較複雜的國族問題處境時,他的思考方式其實跟我們習以為常,或是我們認為一般在這種處境中的人會想的東西不一樣。
引用通告: 枯草新芽──再見陳舜臣(下) | 游擊文化/公共冊所
引用通告: 枯草新芽──再見陳舜臣(上) | 游擊文化/公共冊所
引用通告: 《青雲之軸》、《憤怒的菩薩》、《半路上》──陳舜臣大時代三部曲專題 | 游擊文化/公共冊所